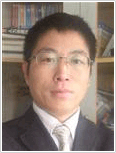企业维权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企业维权
无效劳动合同处理规则的分析及适用(上)——以《劳动合同法》为对象
2011-10-30 11:46:29
【内容提要】《劳动合同法》规定了过于宽泛的无效劳动合同的法定事由,同时在劳动合同无效后果的处理上,该法对已经发生的劳动权利义务采用的是合同相对无效的处理方式,即将已经发生的权利义务规定为可变更的权利义务,而对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劳动关系的处理上,则将劳动关系是否继续维持规定为当事人的一种权利。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从价值角度考量,缺乏正当性;从规范角度考量,缺乏合理的逻辑。因此,有必要运用法律解释学所提供的工具,赋予该法相关规定以更合理且合乎逻辑的含义。
【关 键 词】劳动合同 处理规则 法律适用
但凡合同,均有合法性问题,在传统民法领域,对因违法而被否定了效力的合同称之为无效合同。用以反映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也不能例外。但是,由于劳动关系本身的特殊性,劳动合同效力问题特别是其中无效劳动合同处理规则的设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国现行法律在无效劳动合同的法定事由及其后果处理方面,作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规定。
关于无效劳动合同的法定事由,我国《劳动合同法》作了非常宽泛的规定,该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该条第二款规定:“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关于无效劳动合同的后果,我国《劳动合同法》基于劳动力的给付不能返还的特点,又作了特殊的规定,针对已经履行完毕的部分,该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数额,参照本单位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针对尚未履行的部分,该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和第三十九条第五项则分别规定,用人单位有因该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劳动者有因该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用人单位同样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关于无效劳动合同的上述规定,存在着诸多理解与适用上的难点,本文试图以案例为样本,以已经施行的《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为对象,就其中的理解与适用问题提出一些个人观点。
一、案例及问题的引出
案例一:一名来自农村未满十六周岁的女孩A某来到城市,用其姐姐的身份证和其姐姐的姓名寻找工作,并被一家小型高科技公司录用,从事前台工作,主要负责处理客户来访接待、来电接转以及其他常规事务。由于这些工作非常普通,故公司为该岗位设定的工资标准为每月1,200元,该公司依法与A某订立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一年。
该公司除了业务人员之外,从事各项行政事务的还有另一名员工,是该公司的行政专员,该行政专员每月的工资标准为4,600元。
在与A某的劳动合同履行到第十个月的时候,一个纯属偶然的原因,该公司发现A某使用的是他人的姓名,并且进而发现A某被录用时年龄尚未满十六周岁,由于不知如何处理,该公司没有当即采取行动,等到与A某的合同期限届满时,该公司未再与A某续订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就此终结,此时,A某已经年满十六周岁。
经“高人”指点,A某要求该公司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以公司行政专员的工资标准作为“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标准,补足其本人工资标准与行政专员工资标准之间的差额40,800元,理由是该公司内“相同”岗位的除其本人之外别无他人,所以只能参照“相近”的岗位,而该公司行政专员所从事的,也是公司内的行政事务,而非主营业务,故行政专员岗位是该公司内部唯一与其岗位“相近”的岗位。
案例二:某公司录用B某为其公司产品研发部门员工,双方订立了三年期限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为每月3,300元。由于B某工作卓有成效,该公司多次为B某涨工资,至第三年时,B某每月的工资标准已经增加到了5,000元,但B某工资标准每次增加的同时,双方均没有以书面方式记载工资变更的内容。
B某受到更高待遇的诱惑,决定跳槽,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同时B某发现,该公司规章制度中有公司需要员工加班时员工不得拒绝否则作旷工处理的规定,经研究,B某确信该规定违法,遂以公司规章制度违法为由,以《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为依据提出辞职,并要求公司按照该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支付其经济补偿金。
该公司最终同意支付B某经济补偿金,但计算时使用的工资标准是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即每月3,300元。同时,该公司以B某历次增加工资时双方没有以书面形式记载同样属于违法并应归于无效为由,要求B某返还已经领取了的工资与合同约定工资之间的差额。
案例三:M公司拟招聘一名培训专员,遂发布招聘信息,要求的应聘条件是应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有过培训工作经历者将优先录用。C某有大学本科学历,但没有从事过培训工作,遂由其朋友帮忙,由S公司出具了一份曾在S公司从事过三年培训工作的证明。M公司未能及时发现,遂将C某招为培训专员,双方订立了一年期限的劳动合同,约定的试用期为两个月。
在试用期内,M公司因故未让C某立即从事培训工作。试用期满后,C某正式转入培训工作,此后,C某日益明显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培训工作要求的状况。该公司经过调查,最终发现C某以前的工作经历有假,并为此收集到了相关证据,此时,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刚刚履行到第四个月。
该公司想将C某解雇,但研究后发现解雇手段有限。首先,公司虽然有证据证明C某应聘时申报的工作经历和所持证明的内容均属虚假,从而表明C某是以欺诈的方式与公司订立了劳动合同,但若依《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五项规定将C某解雇,则需要双方间的劳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而按照该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须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法院确认,也就是说,只要C某认为该合同有效,公司一方就先要就该合同的效力问题与C某打一场官司,而按照该公司所在地的实际状况,由于劳动争议处理机构的人员配置与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之间处于严重不匹配的状态,劳动争议案件流程的周期很长,一场官司还没打完,双方之间的合同期限恐怕已经届满,如此操作完全没有意义。其次,如果以C某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雇,按照该法第四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则要先对C某进行培训或者调整C某的工作岗位,C某仍然不能胜任的,公司方能解雇。但公司不能容忍实施欺诈行为的C某继续留在公司。无奈之下,该公司遂以双方劳动合同系因C某实施欺诈行为订立应属无效为由,直接将C某当即解雇。
C某则以公司在劳动合同尚未被劳动争议处理机构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将其解雇属于违法解除合同为由,要求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金。
可以用来揭示劳动关系特殊性极其对无效劳动合同制度影响的,远不止上述三个案例,但这三个案例已经基本能够满足本文对样本的需求。
二、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及其对无效劳动合同制度的影响
劳动关系是一种由资本与劳动力之间为交换目的而结成的具有人身性的继续性关系,这种关系与普通民事合同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首先,虽然和大多数民事合同关系一样,劳动关系也是一种以交换为目的建立起来的关系,但在劳动关系中,当事人交易的标的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即劳动者向雇主转移自己劳动力的支配、使用权,用以获取相应的对价——劳动报酬;雇主则以约定价格获得对特定劳动者所有的劳动力的支配、使用权利。和包含劳动过程的普通民事合同关系的区别在于,后者交换的标的只是一个个具体的劳动成果,这种成果可能是劳动形成的商品,或者是一次特定的服务,例如理发师为客人修理的发型等,在这种情形下,对劳动力支配、使用的权利并不发生转移,仍然由劳动者本人拥有。而前者的特殊之处在于,雇主所获取的,既不是一个个具体劳动形成的商品,也不是一次次特定的服务,雇主支付价金所要获取的,不是具体劳动的成果,而是对特定劳动力支配、使用的权利,这种交换的结果,导致对劳动力支配、使用的权利发生转移。而对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的劳动者来说,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机会将自己的劳动力转移给雇主支配和使用,是其赖以生存的唯一手段。换句话说,拥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是每一名普通劳动者最基本的追求。
其次,既然在劳动关系中当事人交换的标的是对劳动力支配、使用的权利,劳动关系中一个更加重要的特征由此凸显出来,这就是劳动力的人身属性。劳动关系的本质是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但其外观上却表现为雇主与作为自然人的劳动者的结合,原因在于雇主是资本的所有者,劳动者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动力是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能力,与劳动者的人身须臾不能分离,劳动关系一旦建立,劳动者所拥有的劳动力,在规定的期间内将归雇主支配、使用,劳动力与劳动者人身不能分离的特点,决定了雇主支配、使用劳动力的过程就是劳动者本人亲自给付劳动的过程。劳动者给付劳动的过程,是一个劳动力使用、消耗的过程,劳动力一旦被使用、消耗,这部分劳动力即告消失,再予返还实为不可能之事。
在传统民法领域,无效合同制度的引入起着对合同效力作否定性评价的作用,体现的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干预,干预的目的则是为了抑制不正当的交易,以促进正当的交易。鉴于无效合同的交易不被法律承认,不受法律保护,“法律行为当事人所想要的并采取行动让其发生的法律后果不发生”,[1]因此无效合同既不具有向前的效力(自始无效),也不具有向后的效力(永远无效),[2]无效合同不具有向前效力的逻辑后果,自然是双方各自交易所得的返还,无效合同不具有向后效力的逻辑后果,则是这种交易不得继续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民法关于无效合同后果的这种制度安排,即便在其自身领域,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在具有继续性特征的商品交换关系中,如果说无效合同不具有向后效力的逻辑仍然有其存在空间的话,无效合同不具有向前效力逻辑的存在,则已经遇到了需要克服的现实障碍。在水、电、管道煤气、基础电信服务等等具有继续性特征的合同领域,倘若无效合同不具有向前效力的逻辑后果是双方各自交换所得应当返还的话,那么这种已经消费了的资源事实上无法返还,要双方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状况的追求无疑不可能实现,因而需要有更适合于此种关系的合同效力否定技术。
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劳动关系领域,传统民法关于无效合同后果的规则设计,则更加表现出不适应的特点。
如前所述,劳动关系交换的标的是对劳动力支配、使用的权利,而劳动力又恰恰是劳动者赖以换取生活资料的唯一资源,劳动力具有不可储存的特征,劳动力并不会因其长期不被使用而增值(恰恰相反的是,人力资源领域普遍认为,如果一名劳动者长期不工作,其人力资源禀赋将会下降),对劳动者来说,其不被雇佣的期间,就是劳动力被白白浪费的期间。劳动合同无效导致的后果倘若是合同不具有向后的效力,特别是当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在雇主一方时,如果直接否定该劳动合同向后的效力,劳动关系因此而被强制消灭,表面上是要起到促进正当交易的目的,实际上却会强制劳动者退回到劳动力市场,重新寻找出卖劳动力的机会,这种逻辑运行的后果,将会直接损害劳动者最根本的利益。
基于这样的原因,面对劳动合同效力上的瑕疵,是以纠正瑕疵为主还是以消灭这种关系为主来作相应的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一个纯粹法律原理的问题,更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劳动立法的价值取向,本来就应当是在不完全平等的劳动关系双方之间,通过对劳动者一方的倾斜保护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鉴于劳动者最基本的追求首先是要有一份工作,故不应将劳动者一方强行拽离这种不完全平等的关系,生死由之。换句话说,在无效劳动合同后果处理上,应当优先考虑的不是不得继续履行,而是优先考虑当事人是否要继续履行的意愿,如果当事人愿意继续履行的,则应允许在对合同无效因素纠正后继续履行。
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家负有保障并促进劳动者就业的义务,面对劳动合同效力的瑕疵,作为制度决定者的国家,其决策也应当是与该项义务相吻合而不是相背离。
同样,既然劳动力具有一旦被使用、消耗即告消失的特点,再予返还实为不可能,因此对无效劳动合同后果的制度安排,也不可能做到让双方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对合同效力的否定具有向前效力的规则,也不能简单、机械地运用到劳动关系领域。
概而言之,由于劳动关系自身的特点,民事法律关于无效合同既不具有向前效力也不具有向后效力的规则,显然不适合用来调整劳动关系。用以反映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其效力否定规则应当有不同于民事法律原理、更符合自身调整对象特点的选择。(未完待续)
(作者郭文龙,系上海市一中院研究室审判员 责任编辑董礼洁)
[1] [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494页。
[2] 王利明:《合同无效制度的问题》,载中国民商法律网,见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18694。
| 律师名片 | |||
|---|---|---|---|
| 姓 名: | 李居鹏 | 职业证号: | 13101200710869100 |
| 性 别: | 男 | 电 话: | 021-60857666 |
| 所在律所: | 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 | ||
| 业务专长: | 劳动法、公司法、合同法、人身损害赔偿。 | ||
首席律师
站内搜索
业务范围
联系我们
邮编:200030
电话:13651900564
email:lawyer80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