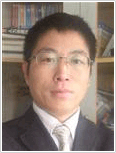人身伤害典型案件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人身伤害 » 人身伤害典型案件
好意同乘施惠者应对搭乘者承担赔偿责任
2012-05-19 11:35:58
作者:钟富胜 胡新
作者单位: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
[裁判要点] 好意同乘中,驾驶员或车主负有保障乘车人人身安全利益的义务,同乘者因乘车受到损害,驾驶员或车主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好意同乘并不能成为驾驶员或车主免除赔偿责任或减轻责任的依据.同时,驾驶员在从事车主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车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驾驶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有重大过失的,应与车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情]
原告(被上诉人):郑友良。
被告(上诉人):邹炜。
被告(上诉人):黄阳生。
2006年3月20日下午,原告郑友良搭乘被告邹炜驾驶的闽F87801号轻型货车由上杭往龙岩方向行驶,行至319国道218KM+780M处,因被告邹炜操作不当,致使车辆失控翻入路边水沟中,造成车上乘员黄松椿、原告郑友良和被告邹炜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原告郑友良随即被送往龙岩市第一医院抢救,经该院诊断,原告的伤情为:1、右股骨运端闭合性骨折;2、左冠折、颌面部软组织挫裂伤;3、颅脑外伤、脑震荡。原告住院治疗至2006年4月29日。住院期间,原告由其妻(系农民)护理,住院的医疗费用为23875.37元。2006年5月24日,原告前往龙岩市第一医院门诊检查治疗,支付医疗费94.7元。2006年3月25日,龙岩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大队(以下简称龙岩交警直属大队)作出第200600173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邹炜对本事故负全部责任,郑友良和黄松椿对本事故不负责任。2006年6月30日,龙岩市法医鉴定中心作出(2006)岩市法医鉴435号法医学鉴定书,评定郑友良已达10级伤残,原告支付鉴定费200元。事故发生后,被告黄阳生以预借方式支付原告治疗费1.5万元。就赔偿事宜经龙岩交警直属大队调解未果后,郑友良遂起诉至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另,闽F87801号轻型货车的车主为被告黄阳生,被告邹炜系受雇于被告黄阳生。
[审判]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郑友良搭乘被告邹炜驾驶的闽F87801号轻型货车,被告邹炜负有保障原告人身安全利益的义务。被告邹炜操作不当致使车辆失控翻入水沟中,造成原告受伤,经龙岩交警直属大队事故认定,被告邹炜负本事故全部责任。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邹炜受雇于被告黄阳生,而且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原告受伤,因此作为雇主的被告黄阳生应承担原告郑友良遭受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被告邹炜操作不当致使车辆失控翻入水沟中进而造成原告郑友良受伤,对本事故有重大过失,负全部责任,因此被告邹炜应当与其雇主黄阳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根据原告郑友良的诉讼请求和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原告郑友良受伤遭受的经济损失有:医疗费23970.07元、误工费38.98元/日X101日为3936.98元(误工费系参照福建省制造业职工年平均工资14229元,从住院之日计算至定残日前1天)、护理费27.44元/日x41日为1125.04元(护理费系参照福建省农业职工年平均工资10017元,按住院41日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10元/日x41日为410元、残疾赔偿金4450.36元/年x20年x10%=8900.72元、伤残评定费200元。原告郑友良系在搭乘被告邹炜驾驶的车辆中受伤,伤残程度较轻,虽造成了一定后果,但并未给原告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因此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1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郑友良主张后继治疗费5000元,因未提供证据,且系尚未发生的事实,本案暂不予处理,待原告实际继续治疗后,当事人可另行主张。被告黄阳生已付赔偿款1.5万元应予扣抵。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17条第1款、第2款、第18条第1款、第19条、第20条、第21条、第22条、第23条、第24条、第25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阳生应赔偿原告医疗费23970.0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10元、残疾赔偿金8900.72元、伤残评定费200元。二、被告黄阳生应赔偿原告误工费3936.98元、护理费1125.04元、交通费50元。上述两项,合计被告黄阳生应赔偿原告郑友良经济损失38592.81元,扣除被告黄阳生已付的1.5万元,被告黄阳生尚应给付原告郑友良赔偿款23592.81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履行完毕。三、被告邹炜应与被告黄阳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两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对被上诉人免费搭乘上诉人驾驶的闽F87801号轻型货车的事实,一审未予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2、闽F87801号车是用于拉货的轻型货车,不是用于运输乘客的运输车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客运合同关系,上诉人不应承担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等强制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应尽的安全保障利益义务。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及民法通则等相关规定,相应减轻上诉人的赔偿责任。一审未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属适用法律不当。3、上诉人免费搭载被上诉人的行为,是无偿的非运营性的帮助行为,对交通事故造成免费乘车人的人身损害,应减轻驾驶员或车主的赔偿责任。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1项、第2项,改判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经济损失38592.81元的70%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郑友良辩称:上诉人既然同意免费搭载答辩人,就应当保障答辩人的人身安全。上诉人邹炜在驾车过程中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翻入水沟中,造成被上诉人人身伤害,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诉人邹炜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答辩人不负责任,上诉人应对答辩人的损失予以全额赔偿。因此,原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允许下免费搭乘上诉人驾驶的闽F87801号轻型货车,双方形成好意同乘关系。好意同乘不能成为驾驶员或车主免责或减轻责任的根据,即使是好意同乘,机动车驾驶员仍负有高度安全注意义务,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操作车辆,不能因为免费搭载而置好意同乘者的生命于不顾。本事故是上诉人重大过失造成的,与被上诉人免费搭车没有因果关系,上诉人主张其免费搭载被上诉人可减轻其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这是一起因好意同乘而引发导致受惠人人身伤害的赔偿案件。此案摆在法官面前的问题是:该案究竟是合同法律关系还是侵权法律关系?责任的承担是否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同时,好意同乘即免费搭乘能否减轻或免除致害人的赔偿责任?好意同乘是否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是否受相关法律调整?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为此,笔者围绕上述几个法律问题进行阐述。
一、好意同乘概念剖析
好意同乘也称搭便车,是指驾驶员(车主或运行人)出于好意,无偿地邀请或允许他人搭乘自己的车辆。好意同乘属于好意施惠行为的一种,好意施惠行为最早由德国判例学说将之称为Gefalligkeitsverhaltni,梅迪库斯在《德国民法总论》中称之为情谊行为,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称之为好意施惠行为,黄立称之为施惠关系。可以说,以上名称都从这类行为的目的或者动机出发,体现了其与一般行为相比的特殊性。遗憾的是,目前理论界尚未对这类行为给出明确的概念。
笔者认为,情谊行为、好意施惠、施惠关系还是施惠行为都不是法律术语。它们只是出于良好动机而无偿为他人提供某种利益的一类行为的总和,是对社会生活中一种普遍现象的高度浓缩和概括,具有无偿性、增进情谊的目的性特征。笔者认为以采用王泽鉴教授的观点为妥,称之为好意施惠行为,而对于该行为中的搭便车行为称作好意同乘。本案被告邹炜在驾驶小货车过程中免费搭乘原告就是属于好意同乘。这种行为不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活动密切联系,而且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氛围中也是应该大力提倡和弘扬的传统美德。
二、好意同乘行为的定性分析
讨论好意同乘行为的性质,就必须严格区分好意同乘行为本身和好意同乘行为带来的后果,对行为的定性不能受行为后果的影响。笔者认为,好意同乘行为本身是一种基于当事人之间的感情(情谊)而发生的不受法律调整的社会行为,因为好意同乘不符合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第一,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件,表意人将自己的意思表示于外部而为他人所知,法律直接根据其效果意思赋予其法律效力,所以判定一个行为究竟是不是法律行为,首先是看其是否具备意思表示。第二,法律行为虽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但人们基于内心的意思而发生的行为,未必都是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必须是人们基于内心意欲发生的一定私法效果的意思,即意在追求一定民事法律效果,具有受法律约束的意思,并表示在外的行为。第三,好意同乘虽有意思从事这一行为,但其实施行为的目的只是增进情谊,而非追求法律后果。也就是说当事人之间没有成立法律关系的目的,没有让自己的行为获得法律上约束的意思,如果没有这种意思,就不得从法律行为的角度来评价此类行为。第四,在好意同乘中,驾驶员没有义务将搭车人运送至目的地,甚至有可能遇到急事时掉头回转,把搭车人又抛至路边。此时,搭车人不能要求其继续履行或承担违约责任,因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合同基础法律关系。
综上,笔者认为,好意同乘是一种普通社会关系,是一种纯粹的情谊行为而非法律行为。其特点是,施惠人基于情谊或为增进感情而无偿施惠于受惠人(并无法律拘束力),受惠人对施惠人无履行请求权,受惠人受益并非不当得利。从本案来看,原告能免费搭乘被告邹炜驾驶的汽车是源于相互间的情谊和增进彼此感情才发生的好意施惠行为,彼此间并无任何约束力,该行为不属于法律行为,是中华民族乐善好施传统美德的一种普通社会关系,彼此间亦不可能构成合同法律关系。
三、好意同乘引发交通事故纠纷的责任承担
上述几点已阐述了好意同乘是一种基于相互为了增进感情或情谊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该行为本身并不存在受法律调整的问题,但当好意同乘的后续行为给受惠人造成损失时,已超出了好意施惠行为本身的范畴,法律应对此造成的损失加以调整。目前在审判实践中,有人将好意同乘行为以双方达成的契约(合同)来规制,认为双方是自愿达成了一种协议,彼此应按合同来进行约束。对此,笔者不能苟同。侵权行为法以权利保护为宗旨,当好意同乘造成受惠者损害并构成侵权时,完全应该运用侵权法加以调整和约束,且侵权法的适用一方面对施惠者(运行者)先前的施惠行为不加干预,另一方面通过侵权制裁来制约施惠者的损害行为,起到保护和协调双方权益的积极作用。
(一)好意同乘中造成交通事故构成侵权的归责原则
根据民法通则中有关规定并结合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理论,侵权行为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两大基本类型。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加害行为;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存有过错。侵权行为法以保护权利为目的,对因侵犯权利所造成的损害可以请求赔偿,所以当施惠者的行为对受惠者造成损害并符合侵权行为构成要件时,完全可以引用侵权行为法的有关规定来寻求保护。本案被告邹炜在驾驶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因操作不当致使驾驶的汽车失控翻入水沟中导致原告受伤,被告邹炜的行为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构成侵权。
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原则,其他如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高度危险责任原则、场所责任原则等都有严格的法律明文规定,都不适用于本案的一般侵权行为纠纷。因为其一,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适用于高度危险作业的生产领域,而不适用于生活领域。其二,汽车是否属于高速运输工具尚无定论,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机动车造成第三人损害的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从而说明将机动车排除于高速运输工具之外。其三,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仅适用于作业时对第三人的损害,不包括对自身的损害。所以,好意同乘不能适用高度危险责任的归责原则。场所责任原则也不适用于好意同乘,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的场所责任仅限于住宿、餐饮、娱乐等商业领域,并不适用于生活领域。其四,场所责任原则是一种补充责任,故好意同乘不适用场所责任原则。
(二)好意同乘施惠者侵权责任承担的认定
1、施惠者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下承担全部责任。施惠者在主观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承担全部责任,但如果受惠者在明知施惠者喝醉酒或车辆明显有故障的情形下,仍坚持要求搭乘所造成的损害,则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的过失相抵原则,适当减轻施惠者的责任。而本案被告邹炜在驾驶过程中则明显存在操作不当的重大过失,导致原告身体受到伤害,完全符合一般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原告损害事实存在:住院治疗并导致原告构成10级伤残;被告邹炜驾驶操作不当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重大过失;原告的伤害与被告的重大过失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同时,被告邹炜系车主黄阳生所雇请的驾驶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赔偿责任理应由雇主即被告黄阳生承担,但因被告即驾驶员邹炜存在重大过失,故被告邹炜应与雇主共同对原告的伤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所以本案中原告所造成的损失应由两被告承担1OO%的连带赔偿责任。
2、施惠者为一般过失或双方均无过错时,由受惠者自负风险。在日常生活中,风险无处不在,人们认识到风险,也自愿承担这些风险。当单独从事危险活动时,由自己承担风险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如果与他人共同从事危险活动时,风险由谁来承担?如果受惠者的风险责任由施惠者承担,那么,施惠者的风险又该由谁夹承担?这时好意同乘的施惠者既要承担车辆的其他风险,还要承担同乘者的风险,作为好意同乘者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就可以享受到像车主或驾驶员那样的便利与快捷,而且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与责任,对施惠者来说显然不公平。法律是调整不同群体利益冲突的技术与方法,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是相对的;当利益冲突无法协调时,法律的价值倾向是保护多数人利益,牺牲的是少数人利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牺牲的是个人利益。做好事还要承担责任,与人们的是非观念和评价标准相违背。
因此,笔者认为在本案中,如果被告邹炜尽到了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而不存在重大操作失误仍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或者发生交通事故纯属意外事件,双方都没有主观过错或重大过失却造成了受惠者伤害的情况下,两被告则应当免责,风险由受惠者自己承担。
3、好意施惠者不能因先前的好意(免费搭乘)而减轻或免除责任。侵权人是否可因是好意施惠而减轻或免除责任的问题,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依社会公平观念,施惠人无偿施惠而有侵权行为时,类似于无偿契约,故其责任应相对减轻或免除。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人的生命健康权的注意义务,不能因好意施惠而减轻或免除,仅将其限定于故意和重大过失。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显然混淆了好意施惠行为的主观状态,正因为施惠人仅仅是出于好意这一主观情谊要素,使该行为因欠缺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要素而得到特殊界定,此时,施惠行为本身不受法律调整。当好意通过施惠行为得到实现后,不能再以好意来重复评价其后续行为造成的侵权行为。侵权责任要考虑的是侵权者在实施侵权行为时主观过错对侵害结果的影响,而行为人的好意与行为人的善意注意义务是两个不同的主观范畴,谈到行为性质时,考虑的是好意,谈到侵权责任时考虑的是善意注意义务。因此,好意施惠人的侵权责任不能因先前的好意行为而减轻或免除。
为此,本案两被告在上诉中认为施惠者对受惠者是一种无偿帮助行为,应当减轻两被告对原告赔偿责任的观点不应得到支持。也就是对被告先前的好意同乘即免费搭乘的情谊行为,应当予以肯定;但对被告的后续侵权行为并不能免除其对受惠者的善意注意义务,仍然负有高度安全的注意义务,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驾驶好车辆,不能因为免费搭乘而置受惠者的生命、健康于不顾。
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李居鹏律师团队
交通事故及其他人身损害赔偿专项法律服务简介
| 律师名片 | |||
|---|---|---|---|
| 姓 名: | 李居鹏 | 职业证号: | 13101200710869100 |
| 性 别: | 男 | 电 话: | 021-60857666 |
| 所在律所: | 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 | ||
| 业务专长: | 劳动法、公司法、合同法、人身损害赔偿。 | ||
首席律师
站内搜索
业务范围
联系我们
邮编:200030
电话:13651900564
email:lawyer800@126.com